我们和李霄峰聊了三个小时
看着他抽完了一盒“荷花”
在烟灰缸里挑出没抽干净的烟屁股
再点上嘬两口
让最后的灰烬重生
拍电影网专访导演李霄峰
这就像李霄峰导演的第二部电影作品一样,从最初定名为《追·踪》,四年时间经历了“烈火燃烧”,最终《灰烬重生》。
电话另一头的编剧沈祎,纯粹、直爽。谈到新版本的《灰烬重生》,她直言不讳:“我一直说李霄峰就应该一条路走到黑,不要轻易妥协。”
我37岁了才第一次看《复活》,躺在前进的火车里,书上面写到:有一个贵族叫聂赫留朵夫,他家有一个佣人叫玛丝洛娃。单纯的玛丝洛娃被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诱惑并侵犯之后,开始了她的堕落生涯,而聂赫留朵夫却全然忘记了这件事。多年以后,当他以陪审团身份出席法庭并审判她时,他幡然醒悟。为了赎罪,他决定跟随被流放的玛丝洛娃一起上路。在路上他为了弥补自己的罪过,向玛丝洛娃求婚,却被她拒绝了。而某一天,队伍里的政治流放犯西蒙松跑来跟聂赫留朵夫说:“我要跟玛丝洛娃结婚了,我想娶她。”聂赫留朵夫感到奇怪,说:“这是你和她的事情,你没有必要来跟我说,我会祝福你们的。”而西蒙松却说:“是玛丝洛娃让我来找您的,她说只有您同意了,她才会嫁给我。”
那一瞬间,我看到了这世界上竟然有三个这么“伟大”的人,他们是那么有尊严。也是在那一瞬间,我觉得我们的人物应该也是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,(片中要出现的那本书)就是它了。徐峰(辛鹏 饰)和王栋(罗晋 饰)对这本书是全然不同的两个理解,徐峰用他自己的生命,诠释了一个真正“复活”的灵魂。但是王栋的理解就是:玛丝洛娃为什么会爱上聂赫留朵夫?就是因为他有权有势。
徐峰和余莹莹之间的感情虽然破碎,经历了很多困难,但那却是一个绝对理想的人际关系,简单、纯粹。王栋对萱慧的感情,是一种执念。我记得有一场戏,王栋一掀帘子,萱慧就坐在那,他走过去。那场戏拍完以后,我发了一条朋友圈,写着:爱是什么?爱是空谷足音。一个人走过山谷,你只能听见自己。你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,但是你面前的人不知道。什么样的人能够为了自己爱的人去杀人?这种人要是在古代,就是一个浪漫主义的集大成者,但只不过我们现在在法制社会,没有办法去彻底同情他。一个人执迷到一定程度之后,你觉得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,但他却是最大的浪漫主义者。像王栋这样的人,从农村考到城里,他想要得到这个女孩。而最后他却是一个真正大的悲剧,我认为这种悲剧是很古典的。
我觉得电影的魅力就是有一些未知的东西在牵着你往前走,这是最棒的事。片中的这几个人物,其实到开拍之前,我都觉得还没有真正理解他们,拍的过程中都还觉得,是这样子的吗?直到王栋走到剧院门口,把脸捂在毛巾里,我才知道,原来这个人物是这个样子的。他超乎你的想象,我觉得这个才是电影。我们在墓地的那场戏,徐峰有一句台词是“心软的人未必都善良”。这句词是在开机之前,我和现场编剧赵阳在聊天的时候随口说的。他听到后觉得好,就加到徐峰身上了。其实有时候台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碰撞出来的,你需要像现场编剧这样的一个人,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,才能让电影活起来。我觉得电影银幕是另外一个世界,它要自成逻辑,拥有自己的精神途径。比如塑造人物,我们说王栋是个浪漫主义者,这种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虽然少,但是却真实存在。就像黑泽明拍的《白痴》,女孩站在楼梯上说“友情是不能用金钱来换的”,这句话就特别自然。所以我觉得大银幕不是来反映现实生活的,它有时候是反映我们的希冀。人物的台词要从他自己内心里蹦出来,而不是完全使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。我其实是在拍完之后,才发现我好像没有太遵守常规,但是我并没有刻意地要去打破常规。我希望这部电影第一可以塑造出能触碰到心灵的人物;第二是去寻求电影自身的美感。片中有一个徐峰骑着摩托车路过的大远景,画面上方是重庆的高楼大厦,灯火辉煌,底下就是一片废墟。这一点我还是挺满意的:重庆最美的夜色都在我们电影里。
我不是艺术家,而是更在意电影的工业流程,在电影制作的规格标准上非常严格,甚至是苛刻。我的每一份拷贝,都亲自去电影院进行测试。因为电影本体的建设对我来说是最享受的,所以我喜欢拍摄现场。一到拍摄现场,我整个人都活过来了。电影的第一要位是“拍”,不拍就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电影是个集体产物,一部电影能成功都是因为后面有一帮人,而不是我一个人。我不喜欢强调“作者性”,因为觉得这个事情不用强调,它就在电影里面。不要把导演神化,导演也都是人,是人就有优点也有缺点。就像我下一部片子《风平浪静》的摄影指导朴松日说的那样,“如果导演什么都会,那我们这些主创来干嘛呢”。每一个岗位都很重要,导演这个岗位和其他岗位是平等的。《少女哪吒》里有个长镜头,从走廊里面落幅到一面镜子,那是我们现场场务提出来的。我觉得剧组的气氛就好在这,它让每一个人都有参与感,而不是只在做一份工作。在给《灰烬重生》做前期调研的时候,一位刑警队队长曾经给我说“你们现在拍电影,我认为有三点很重要,第一是真实性,第二是思想性,第三是创造性。”这句话让我非常吃惊。所以,有些时候我觉得搞电影的人,平时生活的也许偏狭了,脑子全在电影上,而实际生活中的很多人,看的特别明白通透。人生阅历很重要,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,是如何跟人交流的,都是在电影院外边,而不仅仅是电影语言本身。不要畏惧权威,为什么要把某些导演塑造成电影大神去顶礼膜拜呢?就像是一定要按照经典电影的方式去拍电影一样。我觉得电影最有魅力的地方,恰恰是它的不可复制性。
我们去西班牙展映的时候,主持人问我是不是受了希区柯克《火车怪客》的影响。其实我们在剧本写到第二稿时,编剧徐展雄跟我提过这个问题。但是我觉得“交换杀人”这个案子可能会发生在西方,但我们国家也会有。希区柯克用他的方式把这种心理犯罪拍的很精彩,但我们也有自己的追求,这是不一样的。余华有本书叫做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》,我觉得你可以把自己放在历史的河流里,但是你是不是还得自己去游?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,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,总归要在自己的土壤上成长。我觉得如果一谈到电影,头上就像是顶了本《圣经》一样,咱就别拍了。你还是要在你自己的环境里,去尝试寻找自己的路。有时候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,可能觉得自己看到了全世界,但是那是巨人的眼光,不是你自己的视线,自己的世界还得靠自己去创造。如果有一天你想要爬上那座山,想要站到这样的位置去看远方,记得别坐缆车,别走索道。虽然坐缆车是快,但是缆车终究是别人搭出来的,我觉得还是得靠自己去探索。
这部电影我们选择的画幅比是1:1.85,是一个很正常的画幅,不像是《少女哪吒》中1:2.35的变宽画幅。《灰烬重生》我觉得不需要做变形处理,因为这些人物本身的魅力就足够了,不需要用变宽去展现人物和环境的紧张感。拍徐峰杀人那场戏的时候,有一个特漂亮的远景画面,是摄影指导中伟在现场发现的。开拍之前中伟突然给我说,从那个桥上看过来太漂亮了,我们就抓紧时间,趁着黄昏还没结束,全部转移到那里去拍。拍墓地那场戏之前,我们在重庆正午12点,40多度的高温下去现场勘景,感觉都要把人的魂魄烤出来了。我就跟身边的中伟说,这场戏全是红光,因为像地狱一样。这个就是本能的直观感受。我们用的镜头是40年代的老库克镜头,墓地这场戏中伟一开始打算用25mm的镜头拍,他觉得25mm已经够极端了。我说既然都到25mm了,你就直接上18mm。18mm镜头拍出来的视觉冲击力,让全剧组都兴奋了。所以我觉得拍电影的乐趣就在这,大家都很享受这种拍摄现场的变化。
我觉得这一次我还是挺放松的,不像第一部电影出来的时候紧张。我感觉电影跟观众之间是平等的,观众有权利喜欢你的电影,也有权利不喜欢。所以我认为电影跟观众之间其实是交朋友,我当然希望能交到朋友,但是交不到怎么办?我只能感到很抱歉了,那就是我们缘分没到吧。导演不要觉得自己高明,也不要小看观众,别老想着去教育观众。我觉得无论人与人之间,艺术跟人之间,还是电影与人之间,始终是一个平等的关系。在之前的版本中,徐峰与余莹莹中间十年的过程是没有的。但是在国内放了两场之后,大部分观众都不理解徐峰为什么回到斯城,他们认为是徐峰嫉妒王栋有车有房,有完整的家庭,社会地位比自己高。对观众的这种误解我有点苦恼,后来老同学马媛媛(《灰烬重生》总制片人)跟我说,要不你把这段拍出来吧。所以后来我们就去补拍了这段过程,才有了徐峰扇了余莹莹一耳光的那场戏。补拍完这一段后,我觉得拍电影还是一个交流的过程,如果你不敞开心胸,你凭什么让观众自己猜?所以我自己认为这是个进步,也是一种放下吧。
比如疫情结束,我们可能在小西天放映一场,让大家感受一下它的视听魅力,但是放完就结束了,再优秀或者再糟糕的电影,可能在电影院放一个月也就结束了。但是电影的生命在哪?比如说看完电影过了两个星期或者两年,你在跳广场舞的时候,突然想起曾经有一个叫王栋的人也在跳舞,这虽然挺可怕的,但我觉得这个才是电影的魅力。这个可能就是“余味”,观众跟电影的共鸣不见得是一时,可能过一段时间,他才忽然回味过来。就像有的观众跟我说,她是在高考之前看的《少女哪吒》,现在她已经大学毕业了,才明白原来她小时候跟朋友之间的友谊其实就像电影里那样。这部电影在白俄罗斯、爱沙尼亚和波兰等一些东欧国家都挺受欢迎的,但是在西欧就没有太多人喜欢,因为东欧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社会主义传统。我和沈祎当时去萨哈林国际电影节,《少女哪吒》作为开幕影片放映。看完以后,一个俄罗斯本地女孩就走过来跟我讲,她完全看懂了,因为她们国家的90年代就是电影里这样的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共鸣,电影的生命就体现在这。
这部片子没做什么参考,所以有点野,我觉得挺好玩的。但是前期工作做了很多,我们做了三轮非常详尽的分镜,但是到现场我们就不带了,就靠现场感受。因为《少女哪吒》是我的第一部片子,我一定要拍完,所以给自己留出了30%的空间去发挥。但是到《灰烬重生》的时候就没有了,这部片子我觉得恐怕得有70%是在现场诞生的。我可能这辈子再也拍不出这样的电影了,又自由,在某些方面要求又很苛刻。我觉得这跟自己的心态有关系,可能真的是岁数大了,变得有点温和了。放到今天,我可能真的不敢说:“我要一个地狱红,一个腐尸绿”。真的不会再有这种状态了,这部电影就顶到头了。这么野的电影我应该是不会再拍了。在这部电影里,我已经把所有的快乐,所有的极致都享受过了。所以我这次的心态变好了,因为心里踏实。我们补拍之后,面临着一个发行问题,我就在思考,之前的版本是不是太凶猛了?太像一个悍匪了,它太野了。如果说有遗憾,可能就是剪掉了很多风格上我喜欢的戏。这部电影现在的时长是87分半,之前电影节版本是114分钟,可能对我来说最理想的是两个半小时。将来有机会我会再剪一个顺序版,让有兴趣的观众再感受一下这部电影。
拍这部电影有一种造梦的感觉,而我觉得其中梦境的很多东西都是沈祎创造的。因为沈祎本身也是一位诗人,她习惯用更直接的本能释放自己的感受力。在沈祎的剧本中,我最开始不大适应的就是幻觉部分。在她的剧本中萱慧出现了幻觉,她幻想此时此刻杜国金还在自己的身边。这个我一开始很不适应,还因为这个跟她吵了一架,后来我发现可能是我太直男了。带着直男的心态,我可能真的不知道萱慧这个角色应该怎样,她又是怎样看待男性的,这个是无法替代的。如果没有沈祎女性视角的介入,我们就不会创造这样的镜头:王栋和萱慧在家里跳舞,跳着跳着镜头摇下去,一双穿着人字拖的大脚进来,镜头摇起来发现是杜国金。我们用实拍创造了一次幻觉。我们电话连线了李霄峰导演在访谈中多次提到的沈祎老师。她不仅是影片的编剧之一,还作为执行监制参与了电影的后期制作。经由她的推荐,电影配乐大师西蒙·费舍-特纳(Simon Fisher-Turner)也加入了这部电影。
在她的陈述下,我们看到了另一面的李霄峰与《灰烬重生》。
影片结尾让王栋与徐峰两个人在夜色中跳舞,导演一开始是否定的。最早在金马影展上就有观众提问:编剧是否有在暗示他们之间有一些暧昧的情感。我在写这场戏时并没有刻意想要营造这样的气氛。不过我觉得观众有权利去联想和丰满他们之间的联系,所以也不排斥。其实写这场戏特别自然而然,并没有什么功能性的设计。首先,这是两个人第一次的见面,始终带着一些戒备心。我觉得他们需要做一些事情,去打破这种尴尬,或者说干脆把这种尴尬放大。其次,王栋对于萱慧和杜国金跳舞时的那种快乐,一直感到失落。他在情感上的很多逻辑一直是错的,想法也比较笨拙,他会觉得如果他也会跳舞,是不是就可以带给萱慧快乐,或者得到她更多的情感回应。这个困惑一直萦绕在王栋心头,以至于他和徐峰在决定了交换杀人的“大计”之后,几乎是下意识地问了这句话,恍惚间他又回到一个情感上憨实的状态。我在最后剪辑的时候建议李霄峰把这场戏放在结尾,其实是有私心的。他们两个在那一晚之后就要去实施他们的计划,各自踏上万劫不复的犯罪之路。但是在舞蹈那一刻,他们两个就像是两个大男孩在玩耍一样,回到很本真的状态。这两个在现实生活中都很孤独,没什么朋友的人,在他们决定把各自的灵魂交给魔鬼之前,我想让他们有那么一刻是纯真无邪的。我希望在电影的世界里,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,在这个命运的十字路口,能不能给这两个年轻人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。我想象他们或许仍还有机会,重写这段历史,重塑他们的灵魂。
2014年,Simon受邀在上海为一部默片做现场配乐,他并没有按照常规的配乐方式去做,而是脑洞大开地运用了很多电子乐。第二天又听了Simon在讲座里分享了他和德里克·贾曼的合作经历后,我直觉《追·踪》可以找Simon来配乐!西蒙·费舍-特纳
李霄峰虽然是一个看起来离经叛道,不喜欢按常理出牌的创作者,但其实他的创作里又很追寻古典的美学;精神内核上也有很传统的一面。他这种古典与先锋融为一体的疯狂,是矛盾的,甚至有些不可调和,并不是常人能理解的。我在德里克·贾曼(Derek Jarman)的电影里看到了他们相似的地方,我觉得只有疯子才能理解疯子。整个配乐过程确实也比我们想象中顺利和高效得多,他们俩几乎是一拍即合的。
毛巾其实不在原来剧本的设定里面,这是我写完剧本之后,写了一篇叫《流浪汉的清泉》的微博。有一天我坐在车里,正堵在路上,开开停停。车窗外一个非常落魄的流浪汉进入眼帘。浑身上下漆黑一片,像矿工一样。他挎着一个破包,偶尔看天,嘴里念念有词。他路过一根电线杆,头也不回;走几步,又路过一根电线杆。忽然他回了头,定睛看着两根电线杆之间的一串长绳。那根细绳上挂满了几十条像是理发店使用的白色毛巾,雪白雪白的,我隔着车窗都好像能闻到那种洗涤剂的味道。我看到那个流浪汉摇摇摆摆走向毛巾,一边走,一边他那像树根一样盘根错节的头发还会飞起灰尘。但他脸上的表情特别开心。他走到毛巾前,用黑色的手一条条地捧起干净到仿佛一尘不染的白毛巾,把它们像泉水一样收集到双手里,然后吸了一口气,整个脸都埋了进去。我被那一刻深深震撼了,我想每个人,不论有多么不堪和落魄,他都有想要变得干净,找回自己尊严的时刻。我很感谢李霄峰把这个场景放到了电影里,在王栋走进剧院的最后一刻,毛巾给了他一个缓冲。当时的王栋已经准备好接受自己最后的结局,去直面萱慧对自己的真实情感。在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刻,他用这个动作来为自己找回最后一点在爱人前的体面。
目前这个时长的版本还是有一些可惜的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,如果李霄峰知道这个电影最终在线上上映而没有时长限制的话,他应该不会剪现在这个版本。如果导演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去实现他自己的想法,他应该会给出一个更贴近之前电影节的版本,甚至是会更丰富的一个版本。现在这个显然是更简洁,更周全的版本,它把故事讲的更清楚了,对观众更加友好了。我觉得有点可惜,因为我看到过他在创作过程中的那种忘我的火花。如果可能的话,我还是期待李霄峰可以摆脱一些导演之外的身份束缚,纯粹回到他最开始的创作状态去考量电影的呈现方式。现在所做的那些所谓友好的调整,其实对于一些观众来说并不能察觉到,而对于另一部分观众又是不公平的。我一直说李霄峰就应该一条路走到黑。他有自己所坚持的东西,那就应该坚持到底。更何况这个世界上,很多表面上的“友好”也不过是海市蜃楼,而那些能照亮少数的,甚至边缘地带的作品才是更可贵的。现实越是无奈和残酷,则让电影人更勇于在电影里追求一个不一样的精神世界,这是电影的魅力。我觉得一个好的艺术家是不应该被所有人理解的,恰恰相反,当一个人被所有人欢迎时,那才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候。
声明: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。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,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,我们将及时更正、删除,谢谢。
文/月亮来源/电影摄影师
原文: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4Vixyj_geke32-B6apKuH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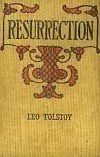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表情
添加图片
发表评论